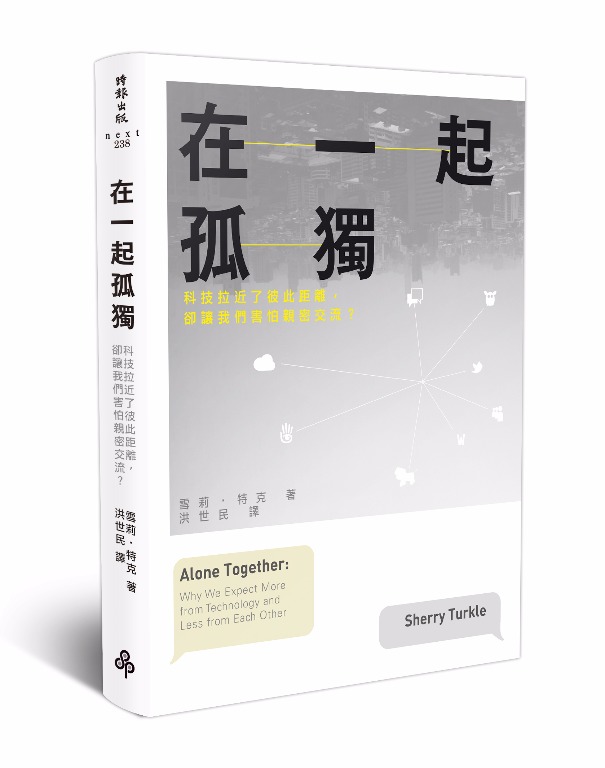現代新科技如雨後春筍般現身,在資訊帶來便利的同時,人與人的感情看似沒有距離,實際上卻更加寂寞。其中有一批幾乎每分每秒都在線上的人,他們是如何利用捉摸不定的網路社群,創造自己的雙胞胎?
撰文=雪莉‧特克
我們碰過十六歲的奧黛莉:說她的臉書簡介是「我的分身」的羅斯福高三生。她正是伊蓮那些生性害羞、喜歡簡訊勝過說話的朋友之一。她手機不離身,有時甚至一面在電腦螢幕上即時通訊,一面用手機傳簡訊。奧黛莉在家裡覺得孤單,她的哥哥就讀醫學院、弟弟才兩歲。她雙親離異,一半時間跟父親住、一半跟母親住。兩家相距車程四十五分鐘,這意味奧黛莉有很多時間在路上。
「在路上,」她說:「這就是我每天的生活。」她把手機視為黏合她的生活的膠水。她母親會打電話給她要她傳話給她爸,父親也依樣畫葫蘆。奧黛莉說:「他們打電話給我說:『告訴你媽這樣這樣……讓你爸知道那樣那樣。』我用手機把一切拼湊起來。」奧黛莉這麼總結她的情況:「爸媽把我和我的電話當成即時通用,我是他們的即時訊息服務。」
就像其他許多告訴我類似境遇的孩子,奧黛莉抱怨母親在她放學或運動練習結束來接她時,心都不在她身上。在這些時候,奧黛莉說她的母親通常專注於她的手機,不是打簡訊就是跟朋友講話。奧黛莉描述了那個場景:她精疲力竭地從體育館走出來,帶著沉重的用品。她的母親坐在她破爛的休旅車上,埋頭講她的電話,直到奧黛莉開車門才把頭抬起來。有時候母親會跟她視線接觸,但一開車上路,焦點又回到電話上了。奧黛莉說:「那介入了我們之間,但我無計可施,她不會放棄它的。就算我已經四天沒跟她講話,我還是得坐在車子裡,默默等她講完電話。」
奧黛莉對母親存有幻想:滿心期盼、苦苦等待她沒有手機的那一天。但奧黛莉認命、放棄了,也覺得必須緩和對母親的批判,因為她自己跟朋友在一起時也有傳簡訊的習慣。
為了避免打電話,奧黛莉無所不用其極:「講電話很尷尬,我不知道意義何在。有太多時候只是重複一樣的話和分享感覺,至於簡訊……我可以在我想回的時候回。我可以回應,也可以忽略,所以真的視心情而定。我沒有什麼事非做不可,不必承諾什麼……我可以掌控對話,也更能掌控我要說的話。」
簡訊能提供保護
沒有人會吐你口水。你有時間思考和準備你要說的,讓你看起來更像你自己。你可以事先計畫,因此可以掌控要怎麼對這個人描述,因為你可以選擇詞語,編輯好再傳出去……當你用即時通訊,你可以刪掉東西、編輯你要說的、封鎖某個人,或登出。講電話的壓力很大,人家預期你會拿住話筒、繼續講下去,那樣的壓力太大了……你得一直講、一直講……「噢,你今天過得怎麼樣?」你得一直想別的事情說,讓對話不會戛然而止。
然後奧黛莉創了一個新詞。她主張簡訊比電話來得好,是因為「對人的限制度(boundness)低得多。」她的意思是在電話裡,她可能知道得太多或說得太多,因此事情可能「失控」。電話沒有明確的界線,她承認:「在以後的人生,我會需要跟人講電話,但不是現在。」打簡訊的時候,她覺得保持了令她安心的距離。如果事情開始朝她不喜歡的方向發展,她可以輕易轉移話題──或者乾脆中斷:「傳簡訊,你可以直接說重點。你真的可以掌控對話要在什麼時候開始和結束。你可以說:『得走了,掰。』你會這麼做……比當你沒有真正非離開不可的理由,但想結束對話時還得長話綿綿、依依不捨好太多了。」這最後一點就是奧黛莉最不喜歡的──結束對話。她解釋講電話「在你沒有真正非離開不可的理由」時中斷對話,是需要技巧的……「好像沒有理由,你就是想停止了。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我也不想學。」
結束電話對奧黛莉來說很難,因為她覺得分離就是拒絕;當別人結束與她的對話時,她會湧起一陣被遺棄的痛,而她推己及人。在別人想結束對話時無動於衷或許看來沒什麼,實則不然。那需要堅強的自我價值感、需要修煉到奧黛莉尚未達到的境界。避開電話比較容易,電話的開頭和結尾對她太困難了。
不是只有奧黛莉如此。她的朋友都很少講電話,而她也表示:「面對面的對話也比以前少了。現在都是『噢,線上說。』」她解釋,這表示「當面發生的事也會在線上發生……友情會破裂。有人打簡訊邀我出去,也有人在線上跟我分手。」但奧黛莉無奈地接受了這樣的代價,而著眼於線上生活的禮讚。
一場成為「分身」的夢
奧黛莉最近的興趣之一是在線上世界表演自己比較社交,甚至打情罵俏的一面。「我想要更像我在線上的樣子,」她說。如我們已經知道的,對奧黛莉來說,建立網路分身跟寫社交網站個人檔案的差別沒那麼大。她說,網路分身「是臉書個人檔案有了生命。」而分身和個人檔案和簡訊、即時通等日常生活經驗更有諸多雷同之處。如她所見,不管哪一件事,重點都是進行「一場你的表演」。
創造分身和打簡訊差不多一樣,你是在創造你自己的人物:你不必當場思考,這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你是在創造你自己小小的理想人物,然後傳送出去。在網路上——例如Myspace和臉書等網站——你也可以放上你喜歡自己的事情,而不必宣揚不好的部分。
你不必每天張貼新的照片。你可以上點妝、穿上你可愛的小洋裝,拍張照上傳;當作你的預設照片,而那就是大家預期你每天的樣子、其實是你為那些人製作的……你可以寫任何關於你的事,這些人不會知道。你可以創造你想要變成的人、你可以說你不想被框在什麼樣的模子裡……或許那在現實生活不適合你,卻擺脫不掉。但你可以在網路上擺脫掉。
和臉書「施與受」的關係
奧黛莉整天與他手機和其上的相機在一起,她成天拍照,然後把照片貼到臉書上,她誇說她的臉書相簿遠比任何朋友多。「我喜歡感覺我的人生在臉書上。」她說,但臉書上的當然是她編輯過的人生。奧黛莉滿腦子都在想該傳哪張照片,哪張最能凸顯她的優點?哪張讓她看來像迷人的「壞」女孩?如果玩身分遊戲是青少年的工作,那奧黛莉整天都在工作:「如果臉書被刪,我就被刪了……我所有回憶可能都隨它而去,付諸東流。別人也貼過我的照片。那些全都會失落。如果臉書毀了,我八成會發瘋吧……那裡是我的天地。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是第二個你。」奧黛莉就在這時這麼形容臉書的分身:「那是你在網路上的小雙胞胎。」
因為奧黛莉不斷重新塑造這個「雙胞胎,」她不由得懷疑被她編輯掉的雙胞胎元素,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臉書會怎麼處理你上傳又刪掉的照片?」她懷疑那些會永遠留在網路上,而這個想法讓她既困擾又安慰。如果每件東西都建檔,奧黛莉擔心她永遠無法逃離她的網路雙胞胎,這不是什麼好事。但如果每件事都歸檔了──至少在幻想中──她就永遠不必放棄自己。這種想法挺不賴的。
在臉書上,奧黛莉認真打造雙胞胎,而雙胞胎也反過來造就她。她描述她和臉書的關係像是「施與受」。情況如下:奧黛莉試用了一種「挑逗」的風格,她獲得臉書朋友的正面回應,於是又加重挑逗的語氣。她試著在動態消息貼文用「反諷、機智」的口吻,反應沒那麼好,所以她收斂了。奧黛莉在測試虛擬世界的分身時,也用同樣修修補補的手法。她建立第一個版本「把東西放上去」,接下來是一連好幾個月的調整,藉由改變表現自己的方式來「看看我可以搭上哪些不一樣的人」。以改變你的分身、改變你的世界。
奧黛莉說她的線上分身提振了她在現實生活中的自信。一如「第二人生」其他許多小女生,奧黛莉讓她的分身比真實的她更符合一般的迷人條件。奧黛莉是個漂亮的女孩,有一頭紅色長髮,編成一條辮子垂在背後。她的辮子和對印花布的喜好賦予她一種老派的面貌。在「第二人生」,奧黛莉選了現代感十足的俐落短髮、身體發育得比較豐滿、妝比較濃、穿著也比較引人遐想——沒有印花布了。那個遊戲的宣傳影片強調這是「連結、購物、工作、戀愛、探索、改變自己、解放自己、敞開心靈、改變外貌、喜愛你的外貌、喜愛你的人生」的地方。但以分身之身分愛你的人生,與在現實生活愛你的人生,是一樣的嗎?
對奧黛莉和她許多同儕來說,答案無疑是肯定的。網路生活既是一種讓生活其他層面更美好的練習,但本身也是一種樂趣。青少年會花時間幫他們線上的自我花零用錢、逛街買衣服和鞋子。這些虛擬的物品有著真實的用處:有這些東西,分身才能過完整的社交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