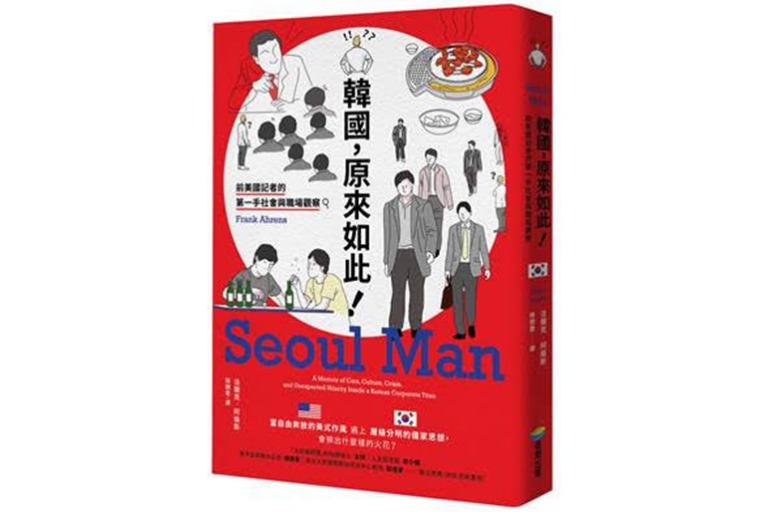韓國職場很拘謹刻板、階級分明,這都要歸功於儒家傳統。上司可以直呼下屬的名字,下屬卻永遠只能以姓氏加職銜稱呼上司,即使下班後也不例外。
起初我不明白這點,也不知道該如何稱呼我上司的韓國頭銜,所以我只喊他「李先生」。這倒無妨。那些階級比我低的同仁比較傷神。
韓國文字跟中文或日文不同,它是以字母為基礎,不是幾千個需要記憶的表意文字。韓文有二十四個字母,簡單有效率,外國人一下午就能學會。
可是,我的姓名是以拉丁字母拼寫出來。所以,如同所有國家,韓國人會把非韓國姓名音譯為韓國字母。問題在於,拉丁語系有些讀音是韓語裡沒有的,反之亦然。韓文裡沒有「F」的音,於是他們用「P」取代。韓語也沒有「K」的硬音,所以他們用一個介於「G」和「K」之間的音替代。韓國人沒有明確區別「R」和「L」音,但他們有一個介於兩者之間的音。基本上,我的姓名對韓國人而言是個地雷。於是,「法蘭克.阿倫斯」在我名片上變成「프랭크에이렌스」。如果你根據這些韓文字母拼讀,聽起來會像「普朗古.阿里朗茲」。
我有些韓國同事會給自己取英文名字,比如我團隊裡的室長班。我當然比較容易記住同事們的英文名字。只是,有些韓國同事並不知道其他韓國同事的英文名字,於是經常發生以下狀況。
我說:「威廉告訴我……」
我的韓國同事問:「誰?」
「威廉。」
「威廉是誰?」
「就是海外市場部那個。個子很高,很風趣。」
「喔,你說的是大玹。」
「大概是吧。」
最後,我用簡簡單單五個字,把狀況搞得更複雜:「叫我法蘭克。」
打從上班第一天起,我就對幾乎每個人說了這句話。這麼做只是為了在團隊裡營造人人平等的感覺,縮短階級距離,把自己新手主管的姿態壓低一點。換句話說,我意圖在東方文化裡打造西方職場。
我進現代初期犯下的錯誤不在少數,這是其中之一。
「叫我法蘭克」讓我團隊裡某些成員感到不自在,也稍微侵蝕了我的階級與地位。他們不想喊我法蘭克,不只因為感覺不太對,更因為這讓他們覺得自己的上司地位低於其他主管。
在這個職場裡,對彼此鞠躬是慣例,從在電梯裡對階級比自己高的人快速點頭,到對來訪貴賓九十度鞠躬。地位至高無上。「叫我法蘭克」不值一文。
語言之外的隔閡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聽部門裡的人提起我的「美國口音」時,內心多麼困惑。「什麼口音?」我問,「我們沒有口音。英國人有口音、澳洲人有口音,連加拿大人都有,就是我們沒有。」對我來說,英國口音偏離標準發音,而標準發音就是沒有口音的美式英語。可是在韓國人和全世界大多數人聽來,美式英語只是英語的另一種口音。
這個醒悟對我造成的震撼,超越我在語言方面的無知。雖然當時我沒有發現,但我的回應其實暴露自己內心的想法:美國是全世界的標準。不只在英語方面,而是在所有事物上:政治、權力、運動、娛樂、財政,一切的一切。這是美國的世界,其他人只是陪襯的配角。
原來我的溝通不良不是因為我的美國口音,也不是因為我不會說韓語,而是因為我沒能了解韓國的基本規矩:儒家傳統與韓國特質(Koreanness)。
如果你想定居韓國,就算你不學韓語,也要試著弄懂這些規矩,或至少知道它們存在。
這很重要,也是基本禮貌。如果你要在韓國做生意,或跟韓國人做生意,這更是不容忽視。
儒家傳統的孝道並不侷限於家庭關係。它已經擴大為「尊敬長輩或上級」的概念,深入韓國社會每一個角落:從工作場合上司與下屬之間形同父母子女的關係,到幾乎不可能平等的商業契約。這是儒家傳統的「尊卑」觀念,不管是在年齡、階級、收入、地位或任何方面,一個居上位、另一個居下位。從地理政治的角度來看,這可以追溯到古代。當時中國地位尊貴,地位卑下的韓國要向中國朝廷進貢。它甚至延伸到今日的韓國契約,公司居上位、員工居下位。於是,你永遠知道自己的位置。這也是為什麼初見面的韓國人可能會問你的年紀。雖然以西方標準來看,這樣顯得很不禮貌,但他們無意冒犯。相反地,他們只是想知道誰比較年長,依此判定你們之間的尊卑次序。至少,部分原因是為了知道該怎麼稱呼你。
喝酒不醉犯大忌
有關喝醉酒這件事,西方人一點也不輸給亞洲人。只是,我很快就發現,亞洲人不是平白無故喝醉酒,或者,套句他們的說法,這叫「飲酒文化」。亞洲人喝醉酒是為了增進辦公室裡的團隊合作、提升生產力,在同事之間建立真正的情誼。這種現象最讓西方人困擾的不是無節制的飲酒,而是公私領域界線的瓦解。在韓國的公司餐會上,煤炭爐上的美味牛肉滋滋作響、綠瓶燒酒一罐又一罐乾掉、你來我往地敬酒、說笑打鬧,當然,還要續攤K歌,彼此的感情因此鞏固起來。隔天到辦公室,大家帶著同樣的宿醉,在吸菸區互相安慰。有個現代主管對我說:「每個人都一樣醉,每個人都一樣。」如果你沒喝醉,或不肯喝,就會害其他人不自在、破壞和諧,讓他們覺得你自命清高。公司餐會背後的驅動力是韓國社會永不停歇的競爭。喝酒的人常會問酒伴:「你喝了幾瓶燒酒?」另一個人也許會神氣地回答:「四瓶!」問話那人就會還以顏色:「每個小時四瓶嗎?」
我向幾個專家討教。有個在韓國住了很多年的美國女性告訴我,她會趁沒人注意的時候把杯裡的燒酒倒進湯裡,再往杯子倒開水,然後向大家敬酒,那碗湯就不喝了。有個韓國籍主管跟我說,他曾經在燒酒杯裡倒「汽水」,那是一種類似雪碧的韓國碳酸飲料,可是同事發現杯裡有氣泡。被抓包以後,他被罰喝更多燒酒。
最後,我還是想出聚餐的解決之道。當女侍忙進忙出送菜和煤炭,同事們笑著鬧著、勾肩搭背的同時,我幫上司倒酒,也幫身邊的同事倒酒,規規矩矩地盡上班族本分頻頻敬酒。
有一次在晚餐會上,有個韓國同事悄悄跑來坐在我旁邊,靠過來跟我咬耳朵:「我也不喜歡喝酒,可是如果我不喝,我的前途會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