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一個鐘頭內發生的安寧講解、身體評估、舒適照護指導,
因為不能中止死亡的進程,
我得到的是王大姐「沒有評估、診斷、處理」的心靈感知,並呈現在投訴單上。
肯尼斯.格根(Kenneth J. Gergen)在他著名的作品《關係的存有──超越自我.超越社群》中,第二章的篇名是〈太初即有者──關係〉。他在這一章中,借用了保羅‧席涅克(Paul Signac)的畫作《馬賽港巡禮》(View of the Port of Marseilles),說明了「全體等於關係的總和」。關係產生後即有雙方,甚且有三方以上。所有處境,一人無可悉數掌握,而必須與全體協動,也必須共同承擔後果。
醫病的相處自是一種關係,有了迫切的生死問題橫亙其中,關係更是複雜。
每一個照顧的故事,都從我們素不相識,但內心已對諸多事件有著詮釋波濤的病人一家見面開始,而往往一家人中的每個成員的心思,還盡皆不同。
我們自然希望關係能夠順利地建立、擴展,但有時對雙方而言,並沒有那麼容易。
就醫的過程,嘗試一連串聆聽醫療人員紛雜指導與命令的過程,當這些語言與誘發的情緒湧入腦海與心中後,我們試著在理性的空間中,以言語表達回應,但實際上卻無法將一切安置,這甚至是在病痛侵擾下的常態。
也因此,醫病之間也常橫生仇恨與委屈,甚至變成不理智的行動,各有所損,也更明白,信任得之不易,甚至無法靠一人締造,既需努力,也仰賴緣分。
當死亡兵臨城下
那日,一切就從王大姐在診間大門口急切地詢問:「這是安寧的門診嗎?」開始的。
王大姐帶著虛弱、痛苦無比,又只能堅強的母親在外候診。充滿無助和憂傷,但又認為自己一定還能為母親做點什麼的信心,以及對安寧似知似未知的害怕卻又期待,更多的可能是對診間內年輕醫師面孔的陌生和存疑。
畢竟處理死亡這麼大樁的事,或者該說逃避死亡這麼巨大的抗衡,不到白髮年紀,怎能信任對方有足夠能力。
我後來才知道,王大姐一家是個總運用萬般資源而特別獲得關切的家庭,不管從行政流程、候診號碼與安排,甚至是就醫選擇,都是先被打點好的。
如果醫療的面向就只有「盡快看診,以保留珍貴的時間」或「找到最資深、最有經驗的名醫」的話,那她們的資訊與管道都不缺。
然而,這些保證卻在此次不管用。因為死亡兵臨城下,面對的難題不是行政或是醫師的選擇,而是一場人類不可能打贏的戰役(如果面對死亡的心態是對抗的話),因此一切都是那麼忐忑,甚至帶著莫名的慍怒。
名醫投下「安寧」這顆震撼彈
王大姐的母親原本所看診的名醫,在前一周投下了「安寧」這顆震撼彈,但除此之外,沒有隻字片語,也沒有轉介的安排。她們第一次嘗到了無人打點的慌亂。
王大姐的母親全身黃疸,X光顯示她的肝癌已至末期,且肺部全是轉移的腫瘤。以餘命來看,可能頂多算周了。
王大姐的母親知無不答,也明確地表示不施行維生醫療延命,以及想要在家善終的心願。
王大姐並不如母親鎮定,但顯然也只能先信任我。
在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裡,我把先前名醫未能明白告知的消息補全,提供安寧照護的說明、釐清病人的心願、評估家人的哀傷與心理準備,並協助安排安寧居家的服務。
病人家屬的投訴
當下,我已看到了非常明確與強烈的「哀傷」,本於我自己長期的安寧訓練與照護經驗,要能預防高風險或是病理性的哀傷,只有一種方法,就是減少病人與家人的想像和真實病況之間的高度落差。
我們得盡可能把安寧解釋清楚,減輕病人或家屬選擇安寧之後所帶來的疑惑、擔憂以及內疚,並在最短的時間內,讓痛楚不已的病人得到症狀的安適,且留下我們會持續在這裡等待陪伴的承諾。
但女兒們與我恰恰相反。她們不曾接觸過安寧,過去高規格的就診待遇,她們需要的是「高貴的藥物與處置」以及「對她們獲取資源能力的敬重」。生死議題洪流帶來的心理和靈性隱憂,不在她們的考慮之內。
然而,王大姐母親的病情已至膏肓,任何一個安寧或非安寧的醫療人員,都知道醫療已經改變不了病程與生命的長度。唯一能做的,只有舒緩和平安,甚至她的病況在當下究竟有沒有醫療人員處置,都不會改變病人如筆直懸崖般下滑的生命狀態。
於是,我沒有做到的,是用所謂的科技醫療鋪滿我們的共同行動,所以我得到的,就是一句投訴的挑戰:「醫師很仔細地講解安寧,但都沒有關心媽媽的症狀、沒有評估、診斷跟處理。」
在那一個鐘頭內發生的安寧講解、身體評估、舒適照護指導,因為不能中止死亡的進程,我得到的是王大姐「沒有評估、診斷、處理」的心靈感知,並呈現在投訴單上,而當這樣的評價,連結上隔天迅速隕落的生命終點時,這樣的評價就轉換為「如果醫師細心一點,我們就可以陪媽媽更久了」。
人情之中的疑難雜症或可通過關切的電話加速處理,但沒有人能對死神關說,這正是生命最公平的地方。
從日日的投訴到要登報與抬棺
隔日,瀕死症狀出現。
雖然母親在前一日的門診中,清楚表達希望在家善終,但那仰賴家人的共識與臨終陪伴的堅定意志與願意學習照護技巧的能力,在這個家庭中,不具這樣的條件。
因此,如同我的預期,她們急迫地呼叫救護車,回到醫院。
安寧團隊也如常運作了起來,且因為前一日看診中的預先準備,她們很快地進到安寧病房,接受到舒適的照顧。
這其實也是安寧照護最困難的地方。善終的優勢永遠是給有準備的人,而不是有地位的人。
哀傷無處投遞,從日日的投訴到要登報與抬棺。
王大姐向公共事務室的同仁訴說:「要不是我聽了名醫的話來找安寧,要不是醫師不細心,甚至不出現,要不是我讓媽媽吃了所謂會舒服的藥(嗎啡)……媽媽就不會走了。」
最後,她要求「醫院和醫師到靈前致意」。
經過院方與我誠懇而公開地討論。我們審度,我是否能前去靈堂?可有危險?我的醫療志氣可否會受挫?我對醫病關係的信心是否會一蹶不振?
妥當安排之後,我們採突襲方式,未事先通知,以免有不利我們的情事被悄悄安排。
以副院長為首帶領,氣勢浩蕩地前往靈堂,連公務車停在靈堂前的位置都事先排演,是逃難機會最大的。因為據聞,王大姐的先生有幫派背景,以暴力威嚇談事,更是常有的事。
王大姐在靈堂前一再訴說她覺得自己非常寬容,因為僅僅要求我們靈前致意。因為她寬厚地原諒所有人,因為這些醫療人員還要救人。
她將自己遭受的不公平,化為母親生命的大愛,只希望我們能直面自己窮酸庸俗的醫術,好好懺悔。
同行長官謙和但堅定地致意,尊重對方的情緒,但也不容與事實不合的侮辱。
過程中,出乎意料地是王大姐的先生竟轉換陣營,攔住她的喋喋不休,出言:「醫院來這一趟,我們甚是感謝。母親病重,本就無力回天,最後能在醫院安然離開,相信已是盡力,實在辛苦各位了。」並以手勢護送我們離開靈堂。
可惜的是,我們無從陪伴這個家庭的哀傷
回程,我方眾人尚在愕然中,而熟悉該家庭的公共事務室同仁臆測,許是這位有著黑道背景的女婿,因為傳聞中的風流韻事,而得屢向金錢增援他的太太娘家低頭,在我們抵達靈堂前,他就是個打手,以讓太太與他同站一線。
而醫院長官抵達靈堂後,他自也無須繼續毫無來由與道理地與盡心盡力的醫院和醫師為敵,自然出手消弭當下的緊繃氣氛。
後續未再有浪起。可惜的是,我們無從陪伴這個家庭的哀傷。在下回死亡又再次叩門時,這個家庭恐難有餘裕圓滿善終、幸福道別。
處理人之生命必然境遇的醫業,確實難為。
被家庭駭浪捲入的醫療人員,不在少數。擎好那洞察人心的照妖鏡,轉圜關係中的諸多細瑣關鍵,以得全體的最大利益總和,竟也成了醫療學有專精之外必備的工作技能。
從醫是種福氣,然福氣要豐厚,也仰賴逆增上緣時,懂得開悟見性之點滴滋養,而這打磨,實也是醫療人員在陪伴病人出生入死之際,所受病人以生命餽贈的禮物。
宛婷醫師的暖心錦囊
死亡事件經常帶來哀傷。
哀傷是一種疾病嗎?若不是,什麼時候會需要心理資源的介入?而高哀傷風險又是什麼呢?
.在面對喪親的事件時,我們會使用「哀悼」這兩個字,來描述悲傷的人必須面對和經過的歷程。
哀悼的任務和主要目的,是為了有效幫助喪親哀悼的完成,而更主要的目的,是讓喪親者好好地繼續自己的人生。
心理治療師William Worden提出哀悼有四項基本的任務,悲傷的人必須履行這些任務後,才能完成哀悼過程。
這四個任務包括:
一、接受失落的事實(正視對方已經離開)。
二、經驗悲傷的痛苦(願意悲傷、允許思念,讓情緒流動,感覺對方在自己生命中的意義與愛)。
三、重新適應一個逝者已經不在的新環境(調適生活步調、重新承擔責任、建立新的關係)。
四、將情感重新投注在生命中(為逝者的情感與懷念,找到一個有意義的處所,同時也將我們愛與被愛的能力帶回現在)。
.悲傷是一種正常的情緒反應。每個人走完悲傷歷程的長短不同,並沒有一定的期限。
但有些人的哀傷期延宕過久,且有一些病態性反應:如憂鬱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或急性精神病症狀,無法回歸常態性的生活,就有可能是進展為複雜性哀傷高風險族群,必須適當提供關懷陪伴、強化保護因子,及早轉介相關心理資源之專業協助等,避免進一步進展為哀傷困難調適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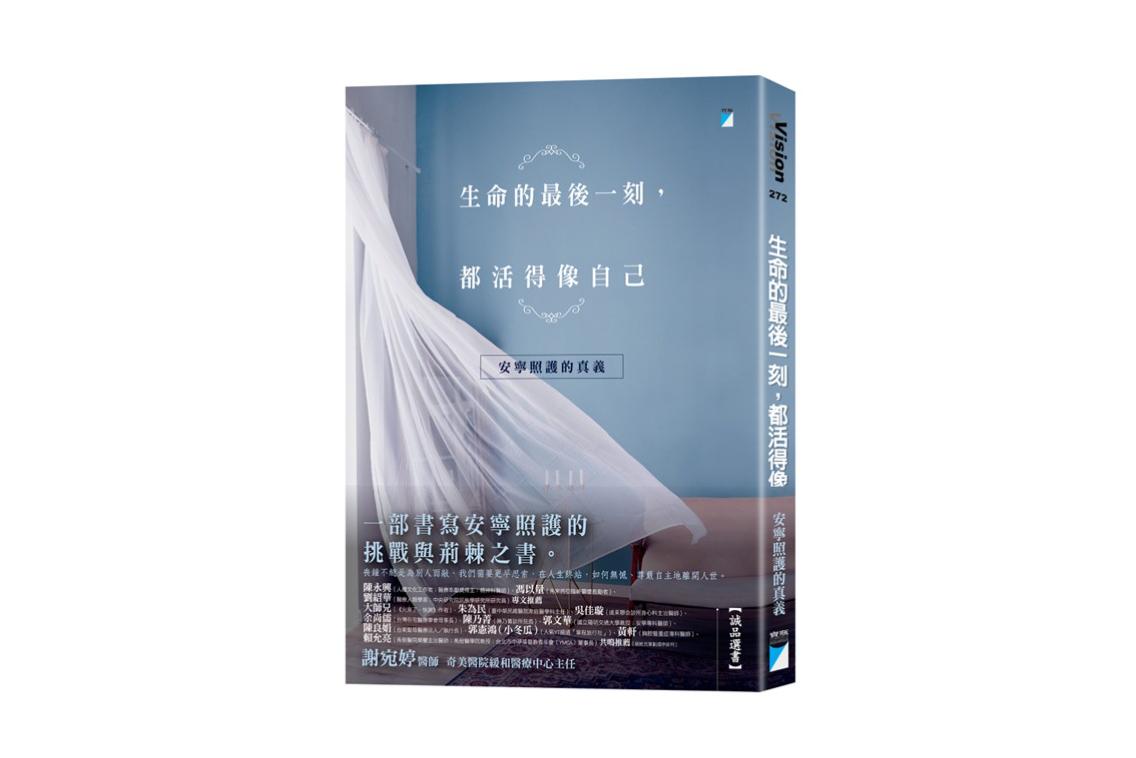
內容來源:《生命的最後一刻,都活得像自己:安寧照護的真義》寶瓶文化授權轉載。